Current Biology | 华方圆
时间:2024-05-27华方圆老师是北京大学生态研究中心助理教授。她致力于森林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恢复,特别是与农业和林业生产相关的土地利用变化。她的研究遵循两大主题:首先,了解生物多样性如何应对人类对森林生态系统的改变;其次,确定保护和恢复干预措施的选择,特别是通过评估生物多样性与其他土地利用需求之间的协同作用和权衡。

华方圆老师
我在剑桥大学完成牛顿国际奖学金的研究后,于2019年5月加入北京大学担任助理教授。在剑桥大学工作两年之前,我在佛罗里达大学野生动物生态与保护系获得博士学位,随后在普林斯顿大学生态与进化生物学系做了三年博士后。我接受的是野外生态学家培训,特别关注森林鸟类如何应对人为影响。
我们的研究主题是了解生物多样性在人为影响下的命运和保护机会。围绕这一主题,我们实验室目前的研究主要有两个方向:
了解野生物种和组合的生态学如何应对人类对森林生态系统的改变
通过对中国一些森林生态系统的实地数据收集,以及对地图产品和现有文献的分析,我们旨在评估人类对森林生态系统的改变--尤其是那些由农业和林业用地驱动的改变--如何影响野生物种的栖息地面积、群落组成和生态。我们主要从局部尺度来探讨这些影响,但在适当的情况下,我们也会考虑其空间模式。除了了解这些影响因素本身,我们的工作还旨在为森林恢复设计提供信息,包括恢复哪些类型的树木植被以及在哪里恢复,以便更好地发挥森林恢复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潜力。
评估和利用生物多样性与其他重要土地需求之间的协同作用和权衡关系
本研究方向的动机是通过解决生物多样性减少的一些根本原因(包括农业和木材生产),以及通过衡量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其他经常受到政策关注的重要环境追求(如基于自然的气候解决方案)之间的 "共同效益 "范围,来确定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机会。与上述研究方向类似,我们将实地考察与理论分析相结合,并在适当的情况下融入社会经济视角,旨在了解工作景观中与生产和利润相关的保护障碍。
目前提出的研究问题包括:森林丧失和退化对鸟类群落(包括海拔和纬度迁徙物种)的影响及其预测因素;不同森林管理和恢复制度之间的最佳土地分配,以最大限度地降低木材生产的生物多样性成本;农林废弃地的保护和恢复潜力。我们的实地考察工作正在中国的四川(西南)、广西(东南)、内蒙古和河北(北部)以及浙江(东部)等省份进行。
我们隶属于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的生态研究所。我们还是一个年轻的实验室,热忱欢迎有理想抱负的年轻自然保护工作者加入我们。
最初是什么让您对生物学产生了兴趣?
和许多野外生物学家一样,我小时候一直对大自然很感兴趣。我认为对这种兴趣有帮助(如果不是有帮助的话)的一个童年经历是在农村长大,就在长江的一条主要支流的平缓丘陵地带,那里虽然以农业为主,但也有相当多的农业。该地区及其周边地区留下的自然景观。那是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大规模农业集约化和城市化尚未展开,而现在这已经完全改变了这一面貌。我家住在一个由一家国营林业企业员工组成的紧密社区里,该企业负责将长江上游采伐的原木运输到下游。实际上,这个社区中的每个人都认识其他人,同龄的孩子都上同一所且唯一的社区学校,很方便并且从幼儿园起就一直是同学。于是,小时候放学后一起奔跑、闲逛就成了我们生活的一部分,而城市又远了,我们的游乐场自然就是周围的农田、山丘、溪流、河岸。我仍然清楚地记得初夏时节,从农田里采摘和倒空杂草豆荚来吹口哨(孩子们会比赛看谁吹得最响),在河里捡拾鹅卵石寻找螃蟹,然后紧张地(因为我对它们有一种原始的恐惧)观察夏天学校树上出现的各种形状和大小的色彩缤纷、看似无所不在的毛毛虫,其中一些体型巨大。
我认为,我对生物的兴趣确实是从这些早期的、直观的自然接触开始的,这也得益于当时当地相对丰富的自然资源。(遗憾的是,当时的各种豆科植物、螃蟹和毛毛虫如今即使没有完全消失,也已经大大减少了;随着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停止天然林采伐,我们的社区也消失了,但这是完全不同的故事,实际上值得称赞)。
当然还有观看自然纪录片(这是我父母鼓励我产生的兴趣),以及阅读杂志上关于自然和人类对自然的破坏的文章。我记得在初中时,杂志上一篇关于亚马逊森林砍伐的文章让我深感不安,并强烈地感到需要为此做些什么。高中毕业时,当我要选择大学的专业时,生物学--关于生物的学科--显然是我的不二之选。
是什么吸引您进入您的特定研究领域?
这又回到了最初吸引我从事生物学研究的原因:我对 "看得见 "的大自然有着天然的亲近感,对野生动物(尤其是纪录片培养出来的)和户外活动有着浓厚的兴趣,并强烈希望避免和纠正人类对大自然造成的伤害。因此,作为一名研究人员,我对生物学的兴趣并不在于生命运作的基本原理,不在于 "看得见 "的本质,更不在于微观层面。当然,我这个门外汉对各种类型和规模的生物现象从来都很着迷;生命在各个层面上精心设计的生存和繁衍策略令人惊叹不已。但是,作为一名研究人员,我必须有真正的动力去发现一些东西,因此我对生物学的兴趣显然是应用性质的,是为保护大自然而从事科学研究。
您有科学英雄吗?
我敬佩的科学家太多了。所以,是的,我有不止一位科学英雄,即使不算那些已经逝去的、在我的领域中永远伟大的名字(比如查尔斯-达尔文)。如果可以的话,我想提及我的两位科学英雄,他们在我职业生涯的不同阶段对我产生了影响。
第一位是美国蒙大拿大学的托马斯-马丁(Thomas Martin),在我攻读博士学位时,他通过生命史视角研究捕食风险的论文给了我持久的启发。当时,我正在努力完成我的论文,试图评估捕食风险及其对猎物行为的影响是否可能是森林退化对森林鸟类产生负面影响的途径。马丁教授的论文很快就成了我的主要学习材料。对于我论文中比较 "基本 "地关注捕食风险影响的部分来说,这些论文提供了引人入胜的例证,说明了生活史理论作为理解此类影响的指导框架的力量,同时也提供了优雅的例子,说明如何通过设计跨越大地理梯度的巧妙研究来检验此类理论。作为我是马丁教授粉丝的一个表示,我记得在我的博士生涯即将结束时,我非常兴奋地发现马丁教授正在扩展他的研究体系,从只关注西半球扩展到亚洲热带地区(我博士生涯的大部分野外工作都是在这个地区进行的,我对这个地区非常感兴趣)。

TOM MARTIN
第二位是我本人认识的美国俄勒冈州立大学的马修-贝茨。我把马特视为我的科学英雄有很多原因。作为一名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自然保护科学家,他拥有景观生态学的深厚理论背景,在生态学(包括基础理论)方面有着令人羡慕的扎实基础--这些基础理论在帮助我们将生态现象概念化方面的价值无论怎样强调都不为过。作为一名领导实验室的资深科学家,他仍然经常以第一作者的身份领导研究工作。他的论文具有可靠的高质量和重要性,以至于我的一位教授曾经说过:"任何有马特-贝茨参与的论文都是好论文。

MATTHEW G. BETTS | Professor,Dept. of Forest Ecosystems and Society,Oregon State University:Lead Principal Investigator, HJ Andrews Long-term Ecological Research Program
我很希望自己也能被视为这样的人!他的工作在主题和方法上都具有令人印象深刻的广度。他立足于野外工作,拥有长期的野外系统,支持对科学问题的深入探索。他是一个有深度的思想家--在我与他的一次面对面交谈中,他指出了不同生态系统因其生物物理特征而在对人类影响的敏感程度上可能存在的内在差异(顺便说一下,这一观点正是他2019年在《科学》杂志上发表的题为: Extinction filters mediate the global effects of habitat fragmentation on animals’ — an instant classi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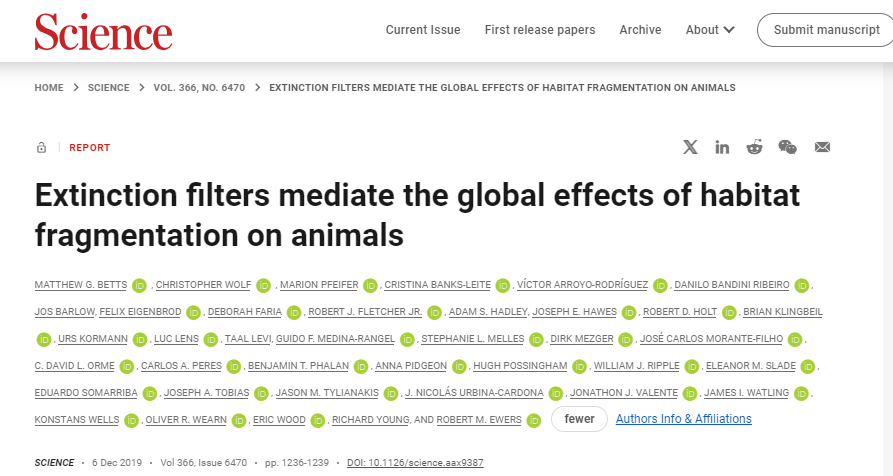
Matthew G. Betts et al. ,Extinction filters mediate the global effects of habitat fragmentation on animals. Science 366,1236-1239(2019).DOI:10.1126/science.aax9387
您有最喜欢的论文或科学书籍吗?
我最喜欢的一本科普读物是比尔-布莱森(Bill Bryson)的《万物简史》(A Short History to Nearly Everything)。这个主题根本不可能完成,但这本书却出色地完成了。我记得第一次读这本书时,我完全被吸引住了,觉得很有趣。这本书信息量很大,同样也很有趣。我会向所有对科学感兴趣的人强烈推荐这本书。
道格拉斯-亚当(Douglas Adam)和马克-卡瓦丁(Mark Carwardine)的《最后的机会》(Last Chance to See)则更接近我自己的领域,讲述了濒临灭绝的濒危物种以及拯救它们的努力。我从来不知道如此沉重、阴郁、经常被当作演讲的话题可以写成一本书,让读者感到如此投入,是的,还很有趣。这本书让人读来津津有味,在欢声笑语之间又发人深省,一定会给读者带来无穷的乐趣。
您得到过的最好的建议是什么?
我从很多导师和科学家同事的建议中受益匪浅,他们的建议也让我倍感亲切。如果非要选一个的话,那就是我的博士合作导师罗伯特-弗莱彻(Robert Fletcher)在我申请博士后职位时给我的建议。
如上所述,我最关心的生态学领域一直以应用和保护为导向。因此,当我完成以行为生态学为主要内容的博士论文时,我一直在纠结自己的博士后研究方向:是乘势深入研究行为生态学,还是 "转行 "研究保护生态学,更直接地提出解决生物多样性威胁的问题。引发这场内心争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越来越有兴趣加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戴维-威尔科夫(David Wilcove)的实验室。我清楚地意识到,在此之前,他们的问题和方法与我的大相径庭--尽管我们都在研究东南亚的选择性砍伐问题。粗略地说,他们的研究与其说是在研究生态机制,不如说是在研究这些机制下的模式,而且还涉及社会经济角度,这对确定保护方案至关重要。
因此,加入戴维的实验室意味着我的研究和科学身份将发生重大转变。显然,这种转变在短期内也是有代价的:我将在一段时间内奋起直追,而且很可能无法及时获得下一份(希望是教职)工作所需的资金。另一方面,我毫不怀疑,能够为紧迫的保护挑战提供清晰、可行的答案才是我真正的使命,而这正是我在此之前的工作所不具备的能力,但这似乎正是戴维工作的意义所在。
我把我的困惑告诉了Robert。他没有给我一个直接的答案,但他说,做(第一个)博士后有两种方法,两种方法都有可取之处。一种是沿着与博士相同的方向深入研究,这样做的好处显而易见,可以在博士后研究中占得先机,并在个人档案中留下一条连贯的工作路线。另一种是做与博士方向完全不同的工作,但这是一个人真正想做的工作,也是其未来研究身份的核心部分。在谈到第二种方法时,他的下一句话让我下定了决心(我在此转述):可以说,博士后是一个人学术生涯中最后一个可以集中精力学习全新知识的重要阶段,因此,尽管有很多明显的缺点,但还是有必要一跃而上。
我最终还是接受了戴维的博士后工作(我很幸运得到了这个机会)。我曾考虑过的种种弊端最终都变成了现实--在我攻读博士后期间,这些弊端给我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但同时也给我带来了极大的收获。
您最喜欢什么样的会议?
我最喜欢的会议类型是:规模大到足以吸引该领域的领军人物,但又足够小,以至于所有会谈都是 "全体 "会谈,每个人都可以参加(换句话说,没有平行会议)。我个人曾经参加过这样的会议(2015 年在土耳其库斯克达斯举行的国际现象学会议),因此这样的会议确实存在,尽管现在可能越来越少见了。尽管我只是为了一个偶然感兴趣的子项目而参加这次会议,而且我在会上几乎没有 "朋友 "可以重新建立联系,但这次会议仍是我有过的最愉快的会议经历,因为我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与其他与会者进行接触和互动。
您希望公众更多地了解科学的哪一方面,是您所在的领域还是整个科学?
我希望公众能够更好地认识到,科学虽然是我们理解真理的最佳尝试,但也很容易受到方法论缺陷和人为错误造成的偏见和错误结论的影响。科学的安全网在于其在证据基础上自我更新甚至自我修正的精神,并由科学界的参与和公开交流来确保。因此,科学的核心追求是避免偏见,在描述客观事实时做到严谨,无论是在单项研究还是在整个特定领域。
关于我的领域,更具体地说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应用问题(减少生物多样性的损失和促进生物多样性的恢复),我希望公众能够更好地将生物多样性损失的可见问题--如物种灭绝、森林砍伐等--与我们每个人的日常选择和行为联系起来。社会中的大多数人可能会很乐意支持保护大熊猫或阻止砍伐亚马逊森林的机制,包括向公司或其他被视为肇事者的实体施加压力。但很少有人意识到,最终使大熊猫和亚马逊河流域陷入困境的力量是我们对木材、农田和自然资源的需求,这与我们资源日益密集的生活方式密切相关。因此,解决生物多样性危机的办法远不止是 "前线 "常常被浪漫化的捍卫野生自然的行动,而是全人类在日常生活中选择消费什么和消费多少,以及最终我们认为自己与自然的关系。在这方面,生态学和保护科学肩负着重大责任,要更好地向公众宣传--让他们了解这一认识,并更切实地让他们知道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可以做些什么来帮助实现这一解决方案。
